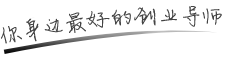盛夏的雨水来得突然而滂沱,大颗大颗狠狠地砸在地上发出没有节律可言的巨大声响。
我被这场雨给吵醒了,在天将亮时。黑了屏幕的手机还在放着歌,最后的一段旋律透过耳膜进入大脑,第一时间我又看见了你的模样。
总是这样,歌声里有你的影子,书本里有你的影子,就连夏季的第一波热浪里也有你的气息。
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它们总能瞬间将我拽回过往,把我困住。
我也很想问问,到底要花上多少时间要怎样做,才能从你制造的回忆里跳脱出来做个从容的旁观者。
在这个下着大雨的凌晨我悲观地想,或许,那是一辈子都不可能的了。
天光大亮,泪涌两行。
一、
我是个特别笨的人,严重点来说是个墨守陈规还很无趣的人,长辈眼中的好孩子应试教育里的模范生。
十六岁以前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可以得到父母老师的褒奖,也省去不少同龄女孩之间争风吃醋的麻烦。
十六岁之后我依旧认为这样挺好的,只是我还想拓宽一下自己涉足的领域和认知别的世界。
循规蹈矩活了十六年,我第一次想要把自己打造成更美好一点的人,更有意思的同伴。Www.Cyewang.Com
王长漫,多年以后,当你经历了人生必不可少的坎坷困顿时,一想到曾经因为自己而改变了另一个人,会不会就觉得有了一点慰籍?身体也不那么冷了?
可惜的是我还没告诉你,我们的缘分就消耗殆尽。
已经过去太久了,我都记不得与你初遇时的天气好不好,只记得人潮涌动着,我被大人们推来推去,最后凭借着娇小的身躯顺势挤到最前面。
那是市中心人流量很大的广场,广场中央搭起了一个简陋的舞台。一台架子鼓,一台音响,一把吉他和一台电子琴,台上三个清秀的少年手握话筒唱着有年代感的歌曲。
流浪歌手在城里很常见,也是那么简单的配置,他们却能走遍天下。我很佩服并且热衷于支持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才在你的面前想找出那个可以投钱的帽子或者罐子,可是等歌都唱完了,我依旧找不到。
这时你跳下舞台站在我面前,看着眼睛还在寻找的我说,“同学你是掉什么东西了吗?”
这样的嗓音,确实适合用来唱歌。燥热滚烫的风浪里,你的声音那么的清爽,独树一帜。无论从前还是以后,我都没听过比这更好听的声音。
我只看了你一眼就迅速把头扭开,心跳砰砰地开始加速,脸正一点点泛红。
我结巴地说没什么,而后一鼓作气拿起你的手把十块钱塞到你的手里,再迅疾地跑开了。
事后想想都替自己觉得丢脸,那个样子真的蠢到家了。但是讲真,你的五官生得极其精致,让我不敢直视。
谁青春的荷尔蒙没有萌动过?在懵懂又新奇的年纪里,甚至是蠢蠢欲动。我花了好几天才能把心情平复,将这种逾越家规校规的心思打包好密封,不让见光。
每天按时上课,认真完成作文,程序上和以前没什么不一样,但是有些已经生成的东西会在潜意识里长大,发酵。
二、
一周后我在校报上看到你的照片才得知,那晚是你和你的乐队在搞路演,是在追求梦想,在实现人生!而不是我所认为的流浪。
好友戳着我的额头咬牙切齿地说,天体运行轨迹你都算得出来,怎么就想不到他们小小年纪怎么可能流浪呢!
是啊!只有我这样只会上升到科学境界的苦读而不在生活中加以思考的人,才会愚蠢地这么认为。

电光火石之间,我又悲哀地想到,那么我给钱的举动会不会弄巧成拙地打击了你们追求梦想的信心?
我趴在桌上哀嚎。
好友见缝插针,“孙怡,你这是扼杀了三个歌坛巨星,罪大恶极啊。”
三天后,我花了整整三天来克服自己的自尊和羞怯,决定向你致歉。
从校报上了解到你的大致信息:王长漫,高一八班,初二与伙伴组成了后海乐队,除了翻唱经典歌曲之外,也自己写歌作曲,唱跳俱佳,校园网上知名度前三,这一届的风云人物,目前加入了音乐协会。
终于等到会议结束,站在音乐室门口的我手里布满了密密的汗,紧紧拽着一个纸盒,里面装有我特意去挑选的道歉礼物。
你最后一个出来,肩膀上挂了把吉他。我叫住你,其余的人一声哄笑,大概对这样的场面习以为常。我也知道,他们以为我是来送情书的。
显然你认出我来了,一句话也不说拉住我的书包带把我带到校外。我那时想你真是粗鲁啊,就算得罪过你,那也不该这样对待一个女孩子吧。
马路上车辆很多,鸣笛声很杂。
我不知道该如何和你讲话,于是斜着眼悄悄看了一下。我看到你微微侧过身,挡住一辆飞驰的小车带来的巨大尘土。尽管没多大作用,我还是感觉到心里涌起的暖意。
为了避开这些铺天盖地的灰尘,你说我请你喝东西吧!
本来应该是我请的,但平时长篇大论的那个我不见了,呈现给你的我是一个木讷的傻姑娘。
迟疑了一会儿我小声地回了一个字,哦。
奶茶店里,我什么也不说地把东西推给你。你好奇地打开,看到里面的东西噗嗤笑了,说,“你是觉得那晚我的嗓子破了?”
店里的桌子是个小圆桌,面对面坐着离得很近,我可以看见你纤长的睫毛。
太紧张了,我双手并上一个头一起摇晃着,说,“不是的,唱歌的人嗓子最重要,防患于未然嘛!”
你拿着那盒金嗓子反复看,“这也太多了吧!”
不多不多,你还有另外两个伙伴呢!
这时你把视线集中到我身上,不用说也知道你的表情在疑惑些什么。我低着头唯唯诺诺终于把目的说了出来。
你忍不住大笑,笑完了你告诉我说是想到了我狼狈逃走的样子……你还说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一直想找机会把钱还给我,但从那晚我穿的校服只能判断是同校,要不是我主动来找,你都打算在校报上刊登寻人启事了。
我长吁了一口气,感叹着还好赶上了,如果寻人启事的联系方式那栏写着王长漫三个大字,估计我也成了风云人物,令整个学校女生发疯的人物。
你听完又哈哈大笑,一点也不拘束,就像老熟人之间的交谈。可能是气味相投吧,在短短一周里我们确实有了老熟人该有的样子。
遗憾的是,知己知彼,各安天涯。
三、
很快我就和你的队友混熟了。吉它手易岑溪,鼓手李鹤,都是另外一所学校能掀起一波潮浪的人物。
我曾无意问过你为什么队友都选择了另一所学校而你选择了只身,你打趣我说,不然怎么能遇见你。
王长漫你知不知道,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开心地以为自己在你心里是可以区别对待的。
每天傍晚你们都会集中在你家那不大东西还很多的木质阁楼里,踏着斜阳的影子排练、作词、编曲。而早早就把作业完成一大半的我总是屁颠地跟着你出校门一起疾步走回你家。
阁楼上的日子,是我一早醒来的期盼和以后想起来都要哭得不可抑制的记忆。
其实一开始结局就显山露水了,只是我没有闲暇注意到。因为我们四个人常常走到一起,所以被别人冠以四人帮的称号。
第一次听到别人这么叫时我就对这个称号生出极度的反感。高二选择了文科的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四人帮的结局吧。
结局之前的年月里,你还是自在如风的少年,踩着滑板直直冲下一道长长的斜坡,湿了汗的刘海被风吹起露出饱满的额头。
无论你有多忙,你都会抽出一点时间来陪我练溜冰。我平衡感不好,足足花了半个月才能脱离你的搀扶,一步一步慢吞吞地移动。
当然,没摔过几次狠的跟头是练不成溜冰 的,但为了能和你一起迎着夜风徜徉恣肆,就算摔得尾骨痛到我一瞬间眼泪就哗哗流出,我都忍了。
终于把溜冰技能掌握的那个晚上,我们坐在学校的草坪里,一直到十一点。
天上的星星稀疏,云层很厚,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你不太把梦想挂在嘴边只是勤恳地行动,但在你仰头看天的眼睛里迸发出明亮逼人的光芒,分明是织就梦想的热血,和一点点哀伤。
这是你的第一次受挫,我也很难过。
几天前你们编排了一首新歌,录制剪辑花了不可计数的时间和努力把它发到比校园网更有空间的一个论坛上,不仅不如以往得到的好反响,还招来网友指责不务正业、水平幼稚、玩物丧志等声音。
你们从十一岁就开始练唱歌,一直练到十六岁,五年时间的押注被质疑被批判,我想平静下的你一定难过得透不过气。
但我不知道能为你做些什么才好,也明白这种悲伤情绪不可以转移,如果可以那么我愿意替你分担。
李鹤他们从小超市买来了几瓶可乐和一些小零食,个个都把手机电筒打开贡献光亮。
尽管深秋的风有些冷了,光也不算好,却是最独特的一个加油打气会。
十点五十三分,我们看到悬挂在头上的天空拨开密云遮盖的月亮,它那么大,土黄色的似糊了一层薄泥。我们抛开腿上的零食忍不住跳起来对着它欢呼、喊叫,像一群狼一样雀跃。
科学家说那晚的月亮是百年来一遇的超级大月亮。我们特意选了个最佳的观赏位置,目睹这历史性的一刻。
总算,没有被我们错过。
后来也有和不同的人守过流星和明月,每一次浮现在脑海里的都是你的脸庞,和红了的双眼。
四、
不久之后我就知道了事情的大概。
作为一个团队你选择了一所离他们遥远得要倒三趟公交的学校,少了很多的排练时间只是为了避开另一个人。而我,不过是因为避开而生产出的附属物。
她对你还真是不上心啊,我如家常便饭般往你家跑了三个月才和她撞到一起。
重振旗鼓的你们比以往拼命多了,严肃起来我都嫌画笔在速写纸上滑动产生的唰唰音会吓跑你们的灵感。
词做了又改,曲改了又编,你们常常忙到顾不上吃饭,只能由我去蛋糕店里买些三明治和牛奶。
就在我捧着一袋三明治走到你家门口,迎面撞见穿着蓬松的毛衣,五官立体富有美感的白玛娜。但吸引我的是那头乌黑亮直的长发,如瀑又似海藻。
她疑惑地走向我,代替我伸出去抓住门把的手,把院门推开。
你是王长漫的朋友?她问。
语气也是淡淡的,和脸蛋上的表情一样让人产生距离感,眼睛里流露有浓重的不屑。
我很不想回答她,但出于礼貌还是淡淡地给了个肯定。她先我一步走进去,轻车熟路地上了阁楼。
看到来人时大家都很吃惊,我明白了她是不请自来。
所有人都停住手中进行的事情,李鹤脸上有着莫可名状的奇异表情看向你,你则自顾自地拐到我身边来从纸袋里拿出一个三明治,坐在窗边的凳子上吃了起来。
有什么事吗?你看都不看她一眼就问。
白玛娜从斜挎的包里掏出一个方形小盒子,
盛夏的雨水来得突然而滂沱,大颗大颗狠狠地砸在地上发出没有节律可言的巨大声响。
我被这场雨给吵醒了,在天将亮时。黑了屏幕的手机还在放着歌,最后的一段旋律透过耳膜进入大脑,第一时间我又看见了你的模样。
总是这样,歌声里有你的影子,书本里有你的影子,就连夏季的第一波热浪里也有你的气息。

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它们总能瞬间将我拽回过往,把我困住。
我也很想问问,到底要花上多少时间要怎样做,才能从你制造的回忆里跳脱出来做个从容的旁观者。
在这个下着大雨的凌晨我悲观地想,或许,那是一辈子都不可能的了。
天光大亮,泪涌两行。
一、
我是个特别笨的人,严重点来说是个墨守陈规还很无趣的人,长辈眼中的好孩子应试教育里的模范生。
十六岁以前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可以得到父母老师的褒奖,也省去不少同龄女孩之间争风吃醋的麻烦。
十六岁之后我依旧认为这样挺好的,只是我还想拓宽一下自己涉足的领域和认知别的世界。
循规蹈矩活了十六年,我第一次想要把自己打造成更美好一点的人,更有意思的同伴。
王长漫,多年以后,当你经历了人生必不可少的坎坷困顿时,一想到曾经因为自己而改变了另一个人,会不会就觉得有了一点慰籍?身体也不那么冷了?
可惜的是我还没告诉你,我们的缘分就消耗殆尽。
已经过去太久了,我都记不得与你初遇时的天气好不好,只记得人潮涌动着,我被大人们推来推去,最后凭借着娇小的身躯顺势挤到最前面。
那是市中心人流量很大的广场,广场中央搭起了一个简陋的舞台。一台架子鼓,一台音响,一把吉他和一台电子琴,台上三个清秀的少年手握话筒唱着有年代感的歌曲。
流浪歌手在城里很常见,也是那么简单的配置,他们却能走遍天下。我很佩服并且热衷于支持他们这种生活方式,所以才在你的面前想找出那个可以投钱的帽子或者罐子,可是等歌都唱完了,我依旧找不到。
这时你跳下舞台站在我面前,看着眼睛还在寻找的我说,“同学你是掉什么东西了吗?”
这样的嗓音,确实适合用来唱歌。燥热滚烫的风浪里,你的声音那么的清爽,独树一帜。无论从前还是以后,我都没听过比这更好听的声音。
我只看了你一眼就迅速把头扭开,心跳砰砰地开始加速,脸正一点点泛红。
我结巴地说没什么,而后一鼓作气拿起你的手把十块钱塞到你的手里,再迅疾地跑开了。
事后想想都替自己觉得丢脸,那个样子真的蠢到家了。但是讲真,你的五官生得极其精致,让我不敢直视。
谁青春的荷尔蒙没有萌动过?在懵懂又新奇的年纪里,甚至是蠢蠢欲动。我花了好几天才能把心情平复,将这种逾越家规校规的心思打包好密封,不让见光。
每天按时上课,认真完成作文,程序上和以前没什么不一样,但是有些已经生成的东西会在潜意识里长大,发酵。
二、
一周后我在校报上看到你的照片才得知,那晚是你和你的乐队在搞路演,是在追求梦想,在实现人生!而不是我所认为的流浪。
好友戳着我的额头咬牙切齿地说,天体运行轨迹你都算得出来,怎么就想不到他们小小年纪怎么可能流浪呢!
是啊!只有我这样只会上升到科学境界的苦读而不在生活中加以思考的人,才会愚蠢地这么认为。
电光火石之间,我又悲哀地想到,那么我给钱的举动会不会弄巧成拙地打击了你们追求梦想的信心?
我趴在桌上哀嚎。
好友见缝插针,“孙怡,你这是扼杀了三个歌坛巨星,罪大恶极啊。”
三天后,我花了整整三天来克服自己的自尊和羞怯,决定向你致歉。
从校报上了解到你的大致信息:王长漫,高一八班,初二与伙伴组成了后海乐队,除了翻唱经典歌曲之外,也自己写歌作曲,唱跳俱佳,校园网上知名度前三,这一届的风云人物,目前加入了音乐协会。
终于等到会议结束,站在音乐室门口的我手里布满了密密的汗,紧紧拽着一个纸盒,里面装有我特意去挑选的道歉礼物。
你最后一个出来,肩膀上挂了把吉他。我叫住你,其余的人一声哄笑,大概对这样的场面习以为常。我也知道,他们以为我是来送情书的。
显然你认出我来了,一句话也不说拉住我的书包带把我带到校外。我那时想你真是粗鲁啊,就算得罪过你,那也不该这样对待一个女孩子吧。
马路上车辆很多,鸣笛声很杂。
我不知道该如何和你讲话,于是斜着眼悄悄看了一下。我看到你微微侧过身,挡住一辆飞驰的小车带来的巨大尘土。尽管没多大作用,我还是感觉到心里涌起的暖意。
为了避开这些铺天盖地的灰尘,你说我请你喝东西吧!
本来应该是我请的,但平时长篇大论的那个我不见了,呈现给你的我是一个木讷的傻姑娘。
迟疑了一会儿我小声地回了一个字,哦。